

“我不和你结夫妻的缘,
但我与你允同修梵行的诺。
我若得遇明师,
必记挂你还在红尘漂泊。
我若得度,必来度你。”
——大迦叶的告别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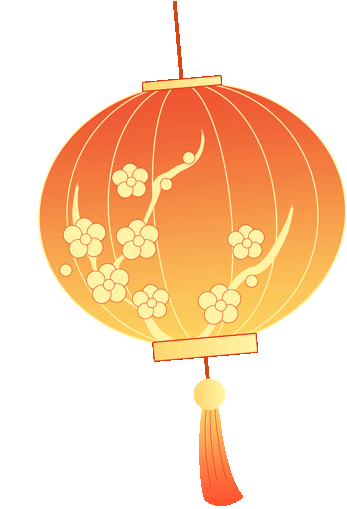
大迦叶,本名毕钵罗耶那,是树下出生的意思。他生长于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,自小聪慧,不爱世间欲乐,惟以修道是从。年岁渐长后,父母为他操办婚事,他用了很多种办法推辞拒绝,但还是迫于无奈,迎娶了家中安排的美丽新娘妙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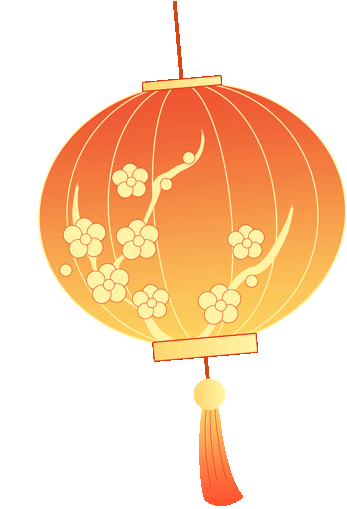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,他们的新婚之夜是在沉默中度过的。当晚,妙贤也是愁眉不展,垂泪到天明,大迦叶问她为什么伤心?妙贤说,我一心修道,被父母逼迫与你成婚,实非我愿。大迦叶听后非常高兴,这竟然是个和自己同样志向的人,乐于清净修行的同修道友做了眷属!他把自己的情况也讲给妙贤听,两人约定:“我若眠时汝当经行,汝若眠息我当经行。”就这样,背着父母家人,他们遵从本心,彼此成就道业。
这是大迦叶对妻子妙贤的“第一次告别”,告别的是还未开始的婚姻。在他的心里,俗世的爱情,不是他今生的任务。他要做的,就是完成觉悟,完成使命。对父母,他们行孝道,扮夫妻;对对方,他们修梵行、为道友。这样的生活,经历12年,他们的因缘逐渐成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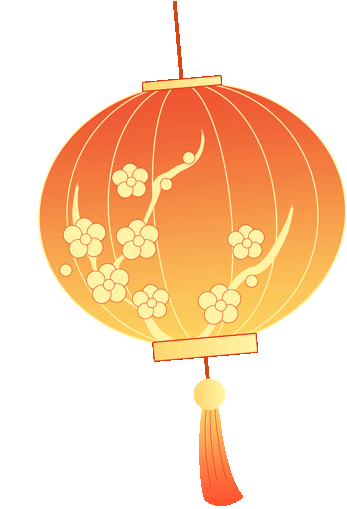
在大迦叶的父母过世后,大迦叶不再有违逆父母心愿的顾虑,他目睹周围的人们在家做事,举手投足,都在造业,而业不尽,就无法从六道轮回中解脱出来,他的心中痛苦无法解决,真的着急了。

与此同时,妙贤听闻家中仆人私下议论,说榨油时死了很多小虫,虽然也有不忍,但必须遵从主人的命令。妙贤立刻命仆人停止榨油,对小虫的悲悯心和满足人类口腹之欲需求的矛盾,令妙贤也觉得当下的处境需要反思。他们需要做出选择了,大迦叶决定离家修道。
他对妙贤说,我走,是为了寻找明师。我若寻到,必来接你。这是大迦叶与妙贤的“第二次告别”。
这是大迦叶对俗世生活的告别,从此以后,他了断了伦常里的进退,一心一意地为修行而自由、深入地用功了。这次告别,也是大迦叶对妙贤的承诺,我不和你结夫妻的缘,但我与你允同修梵行的诺。我若得遇明师,必记挂你还在红尘漂泊;我若得度,必来度你。两人长揖告别,彼此放手,超越了普通世间男女情爱的纠缠,道尽知音同修之间的酬答。

其实他们之间的因缘并不只是这一世,《西土二十四祖纪第二》中记载了大迦叶和妙贤的前世因缘。妙贤曾是个贫苦的女子,为了修补佛像,乞讨集资,筹得金珠,而彼时的大迦叶是位锻金师,二人合力将佛像缺处补足,从此发下誓言,后世常为夫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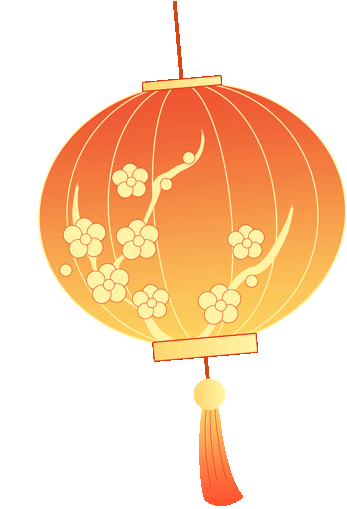
大迦叶离家后,在寻访明师的过程中,遇到了释迦牟尼佛(后文简称佛陀),经过再三的观察确认后,于佛陀座下剃度,并以苦行著称,佛陀赞许他的修行,还曾分半座给他。
其后,在佛陀的姨母兼养母摩诃波阇波夫人再三请求下,佛陀准许了女众出家修行,并成立了比丘尼教团。大迦叶从未忘记对妙贤的承诺,立刻想到把妙贤接来,让她跟随佛陀和比丘尼教团出家修行。

此时的妙贤,在大迦叶走后也为了求法而疏散家财,但误入了外道,正陷入痛苦之中。迦叶带领她来到比丘尼僧团,礼请大爱道上座比丘尼为她剃度正式出家。
但是,因为她的美貌导致外出托钵乞食时总会引起很多人议论,为了明志,她不再外出托钵乞食,常常饿着肚子,日渐消瘦。大迦叶知道后,心中怜悯,征得佛陀准许后,他总将自己托钵乞来的食物分一半给妙贤。此举又受到了一些搬弄是非之人的讥嫌,说:此二人原本就是夫妻,怎可能清净无染?如今同食一粥,当初怎会分床而眠?或许现在仍暗存私情。
讥嫌本是妄语,大迦叶本人阔心无碍,但为了使他人停止口业,也为了激励妙贤,他决定不再和妙贤来往。大迦叶对妙贤传授了法要:“此事应作、此不应作,宜善用心(什么事该做,什么事不该做,应当善用心)”,说完便离去。妙贤当时便发了大勇猛心,夜里即证阿罗汉。

由名义上的凡人夫妻,到少欲知足的优婆塞和优婆夷,再到无欲则刚的出家人、先后证道的阿罗汉,曾经有过夫妻的名分、同修的因缘、道友的恩情,在一次次的告别中,悉数放下,他们也完成了一次次的蜕变和成长。
而大迦叶的成就更不用多说,他与佛法本意相通,佛陀称之为“迦叶功德,与我不异”。佛陀涅槃后他又牵头召集结集佛经,三藏典籍由此得以存世流传,其功不可磨灭。而他在灵山会上的破颜微笑,也是禅宗著名公案,追溯为汉地禅宗思想萌生的源头。
世间的“爱”各种各样,有以“爱”为名的控制和占有,也有甘愿付出的“爱”,但如果都是局限在一人或几人身上的贪执之爱,就是造成生命不断在六道中轮回的根源之一。

从看似富足美满的生活中看到世间诸苦后,大迦叶告别的不仅仅是情爱,他告别了世间欲望、情感的纠缠,但最终要告别的是六道轮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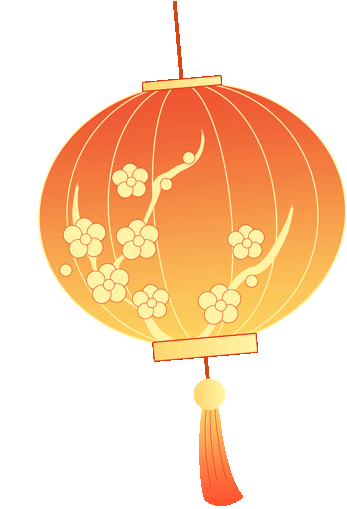
真正的出家人、修道人,是超越男女情爱,舍弃个人贪欲的,不分亲疏高低,对一切众生都能生起无私广大的慈悲之爱。“我若得度,必来度你”,这就是修行人的爱,引导有缘众生听闻正法、精进修行,最终出离轮回、共证菩提!

